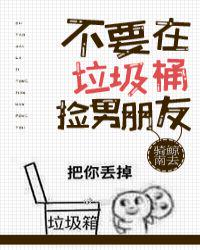第33章 第 33 章
北风信子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DZ读书dzdushi.com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宫车晏驾,举国齐哀。
整个长安城成了白茫茫的一片,戚哀之声不绝于耳,这也许并不是出于对那个从未蒙面的皇帝的感情,而是忽地有种惶惶之感,只能用哭声来表达。
李桑桑等太子妻妾每日前往东内哭灵,文武百官都穿素衣,同样赶到了大明宫行哭踊之礼。
大行皇帝的殡所是在蓬莱殿,他的妻妾妃嫔,儿子女儿在其外的广场处跪了黑压压的一片。
李桑桑紧跟着太子妃崔胭玉,哭灵不是一件简单的差事,光是跪着就足够耗尽体力,更别提还要哭得哀恸。
自徐皇后往下,女眷都面容戚哀。
徐皇后的悲伤不是作伪,她将如花的容颜都哭得憔悴了,面容中隐约带着一丝对未来的惶恐。
然后是华阳公主,这个要强的公主也哭得悲痛不已,李桑桑看了都有些担心。
李桑桑自然也是哭的,在旁人看来,她哭得悲痛,近似于虚伪了。
她与大行皇帝没有什么交情,也轮不到她如此悲伤。
李桑桑不管旁人的忖度,她只是哭得尽兴。
平日里哪里有这样痛快的场合,能够让她哭一场呢?
就这样昏天黑地地哭了三天,众人都是疲惫不堪极了。
三日后,只用早晚哭一回,众人悄悄松了一口气。
崔胭玉扶着侍女的手站了起来,大行皇帝宾天,徐皇后悲痛不已不能管事,宫里的事顺理成章地落在了她的手里。
她强撑精神,走出了光顺门。
不太意外地,她在这里看见了哭完灵起身走出去的李丛。
崔胭玉站定了,她略加思索,唤来宫女给诸位大臣端来几碗汤饼。
崔胭玉亲自过问了年迈大臣的身体,勉励了年轻臣子,然后她站在里李丛跟前。
李丛看着崔胭玉面容憔悴,安慰说道:“太子妃娘娘玉体贵重,千万保重,不要过于哀痛。”
崔胭玉给他端上汤饼:“你不用担心我,也不用怕我,从前的事,我已不再放在心上了。”
李丛默然,然后
说道:“那时,我不该招惹你。”
崔胭玉端庄的表情没变,她像在亲切问候着李丛:“是我看上你的。”
李丛道:“你过得好吗?”
崔胭玉道:“好,当年顺从家中嫁给太子,我便什么都不再想了,如今,我只想牢牢抓住一件东西。”
那日徐皇后送给她的凤簪是如此耀眼,上面榴光般的红,灼灼烧着,冰冷的光将她满心的酸楚冻结起来。
她要去万人之上。
她不再需要梦里的少年。
崔胭玉余光看到身旁有人走过来,她平缓着声音:“昔日父皇曾作诗篇许多,校书郎可整理成册,以便后人时时诵读。”
李丛道:“微臣遵旨。”
崔胭玉和李丛说完话,宫女的汤饼已分完,她转头看去,见走过来的是华阳公主高檀。
高檀这些天哭得很是伤心,走路时,只感到脑子晕晕乎乎,她远远看见崔胭玉和李丛说话,心中隐约有些奇怪,这时候却偏动不了脑筋。
崔胭玉和她略微说了几句话,就走了,高檀站在那里,看着李丛正准备说什么,忽然看见光顺门内匆匆跑出来一个宫女。
她似乎本想去找崔胭玉,但是看到了高檀站在这里,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:“华阳公主,求您找个太医来看看我家良娣吧。”
“桑桑?”
高檀和李丛同时问道。
哭灵结束后,李桑桑看着崔胭玉对自己说了两句什么话,就站起身来走了。
李桑桑也想跟着站起来,腿却像灌了铅一般,死活动不了。
她以为她在开口说话,可是周围没有一个人理会她。
接着她就感到一阵又一阵地发晕。
朦胧中,有人抱起了她,那人不似宫女或太监,要更高大一些,他也是穿着素色的衣服,袖口里有股冷冷柏子香。
暖阁里,有人给她把了脉,然后传来絮絮的说话声。
把脉的大夫走了,那个抱起她的人久久地站在床边看她。
不知过了多久,
她的身旁没有人说话了,她终于可以睡过去。
李丛和高檀赶到蓬莱宫外,并没有看到李桑桑。他们二人问了来往的太监宫人,带着太医匆匆往旁边的绫绮殿一处暖阁去。
太医给李桑桑把了脉,沉吟片刻,说道:“气血两虚,要开点补气血的药。”
看着高檀和太医往一边说话去,李丛走到李桑桑跟前,摸了一把她的脉象。
太医“只需补补”的话萦绕在耳边,李丛将手指收回袖口,指尖微微颤抖。
太医开好了方子,李丛不停颤抖的手也终于恢复了平静。
李丛借口不好在宫中久留,向华阳公主告辞。
高檀不知为何,看着李丛,心中有些不安定。
处理完宫里的事,她在夜里出宫去找李丛。
李丛不在李府,也不在弘文馆,最终,高檀在一处酒肆找到了喝得烂醉如泥的他。
回忆起今日的种种,她只觉得李丛和崔胭玉之间格外蹊跷。
她想到那日清晨,她在街上碰见李丛藏住了一个女子,后来,崔家的马车在街上缓缓而过。
她又想到了那日,李丛看见了崔胭玉的帕子,忽地他有些心神恍惚。
李丛最爱寒梅,崔胭玉的帕子上只绣寒梅。
难道,太子妃和李丛……
高檀捏紧了手心的手,她看着李丛,他的脸上满是失魂落魄。
他口中喃喃说道:“怎么会这样……”
高檀陪伴李丛到了后半夜,最终决心,将醉酒的李丛送回李府。
敲开李府的门,是一个面生的年轻男子,他说他是李府家中的大夫。
高檀将李丛交给了范景。
范景不辞劳苦地为李丛忙前忙后,在李丛清醒一点的时候,终于找到机会问他:“你怎么了?”
李丛握住范景的手臂,他的力度极大,几乎是在掐,他说道:“范景,桑桑是我的妹妹。”
范景将他的手拿开:“你真是醉得没边了,警醒你自己的话,说给你自己听。若这里不是我,你让旁人听
了,只怕会觉得你奇怪得很。”
李丛再次强调:“她是我的亲妹妹,她和我有一样的病根。”
范景这才严肃起来,他盯着李丛说道:“这不可能。”
高桓暂住清思殿处。
他穿着素白的衣裳,脸色苍白,眼底布满血丝。
这几日,他忙得昏天黑地,没有丝毫功夫来伤心他的父亲的离去。
高桓揉了揉眉心,对丁吉祥说道:“让姚公公过来见孤。”
姚公公战战兢兢,不知太子有何吩咐。他担忧过去的举止冒犯了太子,更担心自己就此一去不回。
但面对太子的诏令,他不得不去。
高坐殿中的太子看起来有一些疲惫,但他身上上位者的气息愈发明显。
高桓看着姚公公,没有多说什么:“孤要你找一样东西。”
金玉打造的小盒精致异常,高桓将盒盖掀开,只见里面的东西风干,像是几块褐色的橘皮揉成一团。
就这么一件东西。
姚公公在下面躬身谄媚:“这长生药和大行皇帝无缘,原来是要到殿下身边来。”
高桓嫌恶地看了姚公公一眼,啪地盖上了盒子。
他将盒子递给丁吉祥。
这是高桓在大行皇帝宾天后为自己做的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,他命人将吴美人的墓移到了妃陵。
这件事做得迅速又隐蔽,到了晚间,下起了雨,高桓在这个时候出了宫。
大行皇帝的丧礼繁琐又麻烦,高桓从日到夜,几乎没有合眼,他满身疲惫,却在夜间来到了妃陵。
高桓和李蓁蓁一人一把竹骨伞,走在苔青的泥地上,每一脚,黄浊的泥水会从青苔里渗出来,脚步离开,又重新了无痕迹。
一处新坟,泥土松动,是才迁移不久的。
这是吴美人之墓。
高桓和李蓁蓁依次跪下。
高桓一语不发,却是李蓁蓁在边上絮絮说了许多。
“娘娘的恩情,蓁蓁时刻感念在心,只可怜娘娘走得太早了,蓁蓁无法回报。”
“当年,娘娘最后的心愿,是想要看到蓁蓁嫁给殿下,如今蓁蓁虽不是殿下的妻子,但已然满足,娘娘可以放心,我会好好照顾殿下的。”
李蓁蓁将瓜果贡品放在碑前,烧了一些纸钱,烟火熏到了她的眼睛,她落下泪来。
“娘娘,我们终于熬出来了。”
“你先回去。”高桓忽然说道。
李蓁蓁脸颊上还挂着泪,她有些微怔,楚楚可怜看着高桓。
高桓只是看着纸钱烧出的一蓬蓬火,灰黑的灰烬扑到他的衣裳上,点起了一点火星子。
“你回去。”高桓重复道。
李蓁蓁的脚步渐渐远去,最终,这里寂静一片。
偶尔只有寒鸦的叫声,在这夜晚里,格外凄厉。
而高桓丝毫不觉凄厉,他只感到……安然。
他脸上带了一点追忆的微笑,对着墓碑喊道:“阿娘。”
在这个时候,他和李蓁蓁有着同样的心境:“如今,我不必再在徐皇后跟前装模作样,”他似乎感到好笑,“熬出来了。”
但下一瞬间,他的眼中一片沉沉的黑:“我好恨当年的自己,恨我无能为力。”
他问着墓碑:“阿娘,你想要我做什么。”
高桓这一生,最大的痛苦,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。
那个温柔恬淡的女人在他的记忆中渐渐模糊,他感到害怕,她留下的一丁点的痕迹,就要在他的脑中消失。
她是吴美人,是艳压后宫的徐贵妃身边的一个沉默的影子。
他从不知道她与他的关系,幼时的他,会同高檀高杨一般,对母妃身边的这个女人感到厌烦。
父皇母妃如此恩爱,这个女人却凭空出现在这里,尽管她不受宠,尽管她沉默寡言。
却依旧碍眼。
但这个女人对他却极好。
读书的时候,她会悄悄往高桓的书箧里塞她亲手做的桃酥饼。
她知道高桓喜欢吃。
从小,高桓就能感到宫廷的恶意。
身为宠冠六宫的徐贵妃的儿子,在徐贵妃这里,他收到的是无
尽的忽视和冷漠。
徐贵妃将全部的爱给了高檀,给了高杨,唯独没有给他。
他以为,这是因为徐贵妃生他的时候大伤了身子,所以对他不喜。
从小,没有人喜欢他,高桓习惯了高檀高高在上的嘲弄,习惯了高杨童言无忌的奚落。
当他发现有人在悄悄爱他时,他却不知所措。
高桓从书箧中抖出满书的桃酥渣碎,他对吴美人的爱感到惶恐,感到难堪。
于是高檀怂恿他对这个女人恶作剧时,他没有犹豫。
他将这个女人的糕点器皿全部砸烂,躲在树后悄悄看她难过。
不知为何,高桓也感到特别难过起来。
从小带着高杨排挤他的高檀却在这件事后对他改了态度,这让高桓说服自己,他没有做错。
吴美人从此疏远了他,但高桓知道,她的目光总是在追寻着他。
高桓渐渐长大,他看清了一些隐秘的东西。
比如,徐皇后虚假的亲昵。
不安感和想要迫切寻求认同的心被他隐藏起来,他可以温和端方。
他开始平静地对待吴美人,在这段时间,他活得从容不迫。
吴美人将她的侄女带进了宫,此时,一心忙着教导高杨并和皇后争斗的徐贵妃并不在意。
高桓看着明媚的李蓁蓁,知道,这将会是他的妻子。
总有一日,他会走出大明宫,拥有他自己的藩地,他自己的府邸,他自己的家。
然而情况急转直下。
他的弟弟,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继任者的弟弟高杨,病逝了。
徐贵妃悲痛之余,终于将目光看向了高桓。
高桓感到沉重,他明白他的生活将发生改变。
但未曾料到是这样的改变。
建兴十四年,徐皇后杖责吴美人,据说,是吴美人没有照料好九皇子高杨,才让他一病不起。
吴美人没过多久也离世了。
临终前,吴美人死死拉住他的手不肯放开,她喊他:
“桓儿。”
高桓一怔。
吴美人向来叫他六皇子殿下,这样亲密的称呼,是从未有过的。
吴美人却接着说:“阿娘要走了,你要好好的、好好的。”
李蓁蓁在边上嘤嘤地哭泣起来,吴美人拍了拍她的头发:“可惜了,可惜看不到你们成亲生子的那天……”
高桓只以为这些都是吴美人临死前的呓语,然而几天后,他发现吴美人的宫女在假山中偷偷烧纸。
她口中说着:“娘娘一生命苦,明明诞下了皇子,却认她人做母,娘娘……”
她回头望见高桓,抖如筛糠不敢言语。
高桓冷静地逼问了她。
假山外暴雨如瀑,高桓得知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故事。
当年,极为受宠的徐贵妃生下华阳公主高檀,伤了身子,太医都说,此生再难有孕。
徐贵妃不甘心,可是无可奈何,她说服了皇帝,挑中了吴美人,为她生下了高桓。
本来,吴美人就该殒命,但高桓小时候病弱,离不了生母,徐贵妃只能将高桓暂且交给吴美人,待他长大一些,再做打算。
没有想到,徐贵妃忽然有了孕。
徐贵妃生下高杨之后,有亲子在身边,对高桓将来是否知道身世,不甚在意,她见吴美人安静老实,于是放过了她。
可是后来……
高杨没了。
暴雨天,高桓走在雨中,浑然不觉,他喝了许多酒。
回到宫中,徐皇后秉烛以待。
徐皇后问:“因为李氏?”
徐皇后在处置了吴美人之后,自然不会将李蓁蓁这个隐患留在高桓身边,她准备赶走李蓁蓁,唯一棘手的地方是,她拿不准高桓的态度。
她对这个儿子关心太少。
她今晚才命李蓁蓁收拾行李,就听说高桓不见踪影,晚间来看,却见到他喝得醉醺醺地回来。
高桓沉默许久,说:“对,母后不要赶她走。”
李蓁蓁很快被遣送出宫。
高桓的叛逆自此一发不可
收拾。
他将以往刻意欺负吴美人的女官叫了进来。
他问了李蓁蓁的事,女官小心回答,自以为没有纰漏。
高桓也只是微笑,然而随后,他忽然用手中把玩的匕首,断了女官三指。
他能做的,好像只有这些。
他甚至不能杀一个女官,只因为他始终活在徐皇后的眼皮底下。
天亮前,高桓回到了大明宫。
他迁动吴美人之墓的事没有人知道,大行皇帝驾崩之后,他便强硬地将内宫控制在手中,无论是徐皇后还是华阳公主抑或是其他的藩王,他们的耳目,都失了灵。
几日后,高桓行了登基大典。
理应是要同时封赏后宫的,可是旨意却迟迟没有发出来。
崔胭玉暂住宣徽殿。
整个宣徽殿都有些惶惶不安。
太子妃封皇后,顺理成章的事,为什么这么艰难。
宣徽殿内,不时有隐晦的目光往北边的珠镜殿处望。那里住着良媛李蓁蓁,挨着高桓的清思殿极近。
若说会有变数,那就是因为她吧。
至于良娣李桑桑,她自病后就一直住在绫绮殿,太子根本不曾去见她,明眼人都知道,良娣已经失宠了。
清思殿久久没有决定,新皇帝也不曾召幸任何妃嫔。
眼见这件事焦灼起来,朝臣不免动起心思,折子雪片一般递了上去,却石沉大海。
终于,清思殿有了反应,皇帝召见良娣李氏。
“是良娣李氏,不是良媛李氏?”
大明宫时时响起这样的问话。
李桑桑也稍觉奇怪,她虽然与高桓无声地决裂,但是皇帝诏令,她自是不会忤逆。
她来到清思殿。
她抬头看着高桓,他瘦了些,白了些,身上笼罩着深深的阴郁。
从前,高桓在李桑桑面前是鲜明的,大怒大笑,或是用他审慎的目光灼灼地落在她的身上。
现在,他整个人骤然地冷了下来。
高桓看着她进来,忽然问道:“良娣,皇后之位的人选
,你怎么看?”
李桑桑忽然明悟过来。
他在和她讲他的家事。
选她来问这件事,是因为,她与立后这件事没有关系。
高桓似乎将从前同李桑桑的纠葛彻底放下,现在,李桑桑站在他面前,仅仅是一个游离于立后之事的妃嫔。
而高桓想要找个无关的人,说说话。
仅此而已。
高桓见李桑桑没有说话,又说了一句:“朕想要立你姐姐。”
“陛下,”李桑桑很冷静,“太子妃自入东宫来,从未有过过失。”
高桓不置可否:“你姐姐呢?”
李桑桑却没有正面说李蓁蓁,她只道:“陛下,你想立我姐姐,是一时意气,还是认真想过呢?”
若万事都能遂了高桓的愿,当年太子妃之位都是李蓁蓁的。
可是高桓不能如愿。
现在和当初不同,却没有多少不同。
难道皇帝上位第一件事,就要忤逆太后,废了毫无过错的太子妃,立一个充满争议的女人?
李桑桑猜测高桓要发怒,可是他只是缓缓阖上眼睛。
半晌,他睁开眼睛:“若朕要你在这二人里选,你选谁?”
他的目光沉沉地落在李桑桑的身上,似乎有了实质的分量。
李桑桑知道高桓想要听什么,她说任何话也不会影响结果。
高桓移开了眼睛,说道:“罢了。”
然而她却回答了:“我选太子妃。”
李桑桑觉得,高桓对她大约是要厌恶极了。
但高桓无法强迫她的想法。
若说她选李蓁蓁做皇后,出了清思殿,以后的日日,她都要为李蓁蓁摇旗呐喊。
这就是高桓的目的吗?
高桓似乎倦极了,他摆了摆手,李桑桑欠身,无言地退了出去。
当夜,绫绮殿分外地热闹。
李蓁蓁来绫绮殿,李桑桑是不见的。
那时,李桑桑将吴姨娘做主关了,之后,两姐妹就不再来往。幽居宜秋宫的时候,李蓁蓁从未来看过她,良娣良媛交恶,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