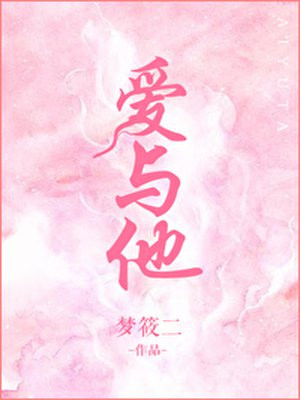天行有道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DZ读书dzdushi.com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他这厢怀疑人生,阮林春则趁这个空档细细打量着他。
之前在走廊上听程夫人介绍,这位小爷单名为栩,表字逸飞——阮林春知道是“俱怀逸兴壮思飞”那个逸飞,无奈前世留下的印象太根深蒂固,很难不让人联想起那位神仙姐姐来。
程栩也的确有几分神仙姐姐的气质,鸦青发鬓,玉色肌肤,此刻只穿着白绫中衣卧在枕上,恍惚叫人以为进了仙人洞府。
还好他没睡吊床,不然就更像了。
程栩被她盯得几分恼火,“你看什么?”
“看你呀。”阮林春答得干脆。
程栩:……
阮林春看他那别扭的小模样,猜想他下一句定是不知廉耻之类的话,索性先下手为强,“你若觉得吃亏,看回来就是了。”
程栩:……
这人的脸皮简直刀枪不入,他彻底被打败了。
不过,他悄悄望了阮林春一眼,觉得这女子并非全无是处:其实,她的眼睛很美,像一泓秋水,平静而澄澈,要不是皮肤太粗糙的话,勉强也能称得上几分姿色。
只可惜此人毫无自觉,非但不加修饰,几乎是素面朝天过来——说好的相亲局呢,难道不该打扮打扮?
程栩尚未发觉,自己下意识将她纳入未来媳妇的范畴内,然而下一刻,他就恨不得像一只炸毛的猫那样跳起来。
阮林春居然把手伸进被子里,直愣愣地放在他大腿上,他就说那一处怎么怪怪的!
程栩满脸羞愤,面红过耳,这下真是可忍孰不可忍,哪有没拜堂先圆房的?他娘找的什么人呀!
阮林春看到他脸上的赤色,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,自己的举动有些误会——话说未来相公居然挺纯情的,难不成还是个童男子?难怪府里连个通房丫头也没有。
她也不想自己形象败坏,遂坦诚向对面解释,“我在摸骨。”
程栩半信半疑。
但阮林春说的是实话,前世她家便是开中药店的,阮林春虽未继承家学,耳濡目染,也略通些医道。难得过来一趟,她总得探探虚实么?虽然她不怕做寡妇,可能当个鲜活的少奶奶,谁又愿意跟块牌位作伴?
拼着让他多活两年,也不枉夫妻一场。
阮林春沉吟道:“世子爷当真是从胎里带来的弱症么?”
程栩此刻已恢复素日的生人勿进,只是耳朵尖仍有点泛红,跟豆沙包上的红点似的。
他淡淡道:“自然。”
这就怪了,若是先天性的小儿麻痹,势必会带来许多后遗症,可据阮林春观察,这位世子爷除了不良于行,其他却是正常的,包括骨骼发育,肢体也很匀称——倒像是中毒导致的肌肉瘫痪。
当然,各人体质不同,可能是她多想了也不一定。只是平国公夫妇爱子情深,生怕他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害,反而延误了病情。他这种情况,若幼时多加锻炼,勤于走动,应该不至于如此严重。
如今只能通过刺激穴道、舒筋活络的办法来一步步唤起他的肌肉记忆,或者尚可一治。
阮林春计议已定,面朝着对面微笑道:“世子爷,改天我抽空来为您按摩吧。”
程栩一脸的“你又想搞什么幺蛾子?”
阮林春为他掖了掖被角,让他躺得更舒坦些,“放心,我没恶意,只是,您也不想国公爷和夫人成天为您担惊受怕吧?”
她看得出,这位世子是个良善人,但,他也同样渴慕自由——否则那天不会偷跑上街去,还被她撞了个正着。
程栩冷声,“你懂治病?”
阮林春坦白,“似懂非懂,就死马当成活马医罢!”
程栩:……所以,他是死马?
阮林春看他默然,便道:“你不说话,那我当你答应了。如此,咱就三日后再见。”
今天她带的工具不足,回去还得查阅些医方,整理一下思路——除了成婚,这便是眼下的头等大事。
程栩默不作声听她安排,反对有用吗?没用。碰到这样自说自话的人,他还是老老实实当只鹌鹑得了。
当然,他私心里也有那么点激动,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,倘若这女孩子能将他医好——就算不能根治,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好。
这种近乎儿戏的想法,他当然是不会告诉阮林春的,免得被她看轻——男子汉大丈夫,和小姑娘一般伤春悲秋,多难为情。
程夫人端着茶汤和点心进来时,就看到阮林春收拾东西准备走人,难免有些恋恋不舍,“不留下来用膳?”
说也奇怪,虽然跟这女孩子才相识,程夫人觉得她怪亲切的。
大概是因阮林春有种直率不加掩饰的吸引力。
阮林春笑道:“不用,母亲还等着我回去呢。”
没过门的儿媳妇,当然不宜留下来用饭,规矩怎么立都是问题。
程夫人也不想被人说闲话,坏了她的清誉,便点点头,“我让老李备车。”
从刚才便被无视的程栩忽然彰显起存在感,向阮林春抬了抬下巴,示意她将博古架上那套青花茶具带走。
自然是证明他并不小气——别说白瓷,就连这种汝窑出产的名贵瓷器他都不放在眼里,说送人就送人。
之所以摔那个双耳白陶瓶,不过图顺手罢了。
阮林春就觉得这人实在很有意思,于是欣然笑纳——这么好的东西,傻子才不要。
程夫人瞧见两人眉毛官司打得热闹,一时间仿佛开启了新天地,这么快就心有灵犀了?难道真是月老牵红线?
阮林春去后,程夫人急忙问儿子,“如何?”
程栩淡淡道:“还凑合。”
唇角微不可见的往上扯了扯,怕被母亲发现,又忙按捺下去。
程夫人:……这便是看对眼了。
*
阮林春下了车,崔氏和阮林絮忙迎上前来,阮林絮问得更快,“姐姐,程家有没有为难你?”
阮林春轻轻抬眸,“三妹很希望我被刁难么?”
崔氏亦有些不悦,哪有这样咒自家姊妹的,真是晦气。
阮林絮:……
她就是随口一问,用得着这样揣测吗?母女俩一丘之貉。
勉强微笑着,“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,不过,国公府的规矩大,姐姐你又是刚回来,我怕你孤身前往,难免诸多不习惯。”
话音未落,就见阮林春身畔那个泥塑木胎似的雕像忽然咳了咳——原来是国公府的老管事。
他长得那么高大,又满面的皱纹,乍一看跟棵叶子掉光了的梧桐树似的。
阮林絮背后说人被揪住小辫子,恨不得寻个地缝钻进去,只管拼命往回找补,“李管事怎么也跟着过来了?快进去说话罢。”
老李头冷冷的道:“不用了,老奴奉世子之命送套茶具,不劳招待。”
阮林絮这才看清他手里那个密密实实的牛皮纸包,哪怕不必打开,她也能猜到必定是上等的瓷器,否则国公府无须这样精心——阮林春究竟使了什么妖法,老的小的都哄住了?
不就是结了桩亲事么?难道国公府这样缺儿媳妇,见了个年轻姑娘便饥不择食,还得百般哄着?
阮林絮想破头也想不出其中情由。
阮林春懒得睬她,径自拉着崔氏进屋去,和她慢慢说起今日见闻。
崔氏不关心瓷器,只关心那位世子对女儿好不好,是否像传闻里说的那样脾气古怪、不近人情?
阮林春笑道:“不近人情是真,倒也未必难以相处。”
像程栩这样的人,总是吃软不吃硬,好好哄着便没事了,说他不通世务,可却知道给见面礼呢。
面对一颗赤子之心,阮林春当然不能食言,按摩的法子她烂熟于胸,不过,要立竿见影,还得有些别的辅助不可。
药酒是最能活血的,不过程栩的体质,一时间未必受得了酒精刺激,阮林絮的灵泉,在原书里却是一味温补的好药。
阮林春问崔氏,“三妹之前酿的那些酒还有么?”
虽然阮林絮刚送过老太太,可凭阮林春的辈分,当然不好去向老太太讨要。
崔氏点头,“有,桂花树下就埋着一坛。”
一面紧张的看着她,“你要酒做什么?”
难道是因婚事不顺,打算借酒浇愁?崔氏这一想可不得了,她年少时虽非贪杯之人,偶尔兴起也想小酌几杯——对女人家的心事,崔氏自认为十分了解。
她当然不能看女儿误入歧途。
阮林春快被母亲的脑洞大开给笑喷了,一手支着腰,免得岔气:“您放心,我哪里会灌黄汤,那是要送人的。”
崔氏这才心下稍定,又怀疑地看着她,“既如此,何不干脆问你三妹,岂非更方便许多?”
阮林春心道,那当然是因为阮林絮不会真心帮她呀,她若是张口,阮林絮定会换成普通的药酒——就算阮林春的婚事妨碍不着她的利益,阮林絮也不乐意她嫁个健康的丈夫。
在她看来,这都是自己和崔氏欠她的,活该用下半辈子的不幸来赎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