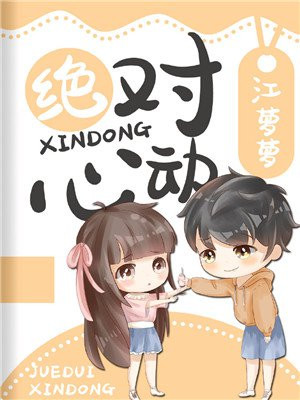庸责己,看起来像男神的指挥家攻VS情商残疾作曲家受(小心逆,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DZ读书dzdushi.com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初冬的午夜零点,月色虽撩人,北风仍凛冽。向来人声鼎沸的夜场被越来越低的气温扯了后腿,人气随着入冬的脚步直线下降,连酗酒成瘾的人都忌惮这如刀寒意,不愿出门买醉。
手机推送的天气预报显示:寒流来袭,请大家及时添加衣物。
穆康裹着大衣,独自一人从沸点出来。酒吧街客人不多,穆康往霓虹灯下一站,立刻成了几位求炮人士眼中的唐僧肉。
一名打扮时髦的短发女孩靠了过去,笑着对穆康说:“帅哥?”
穆康看都没看她一眼,转身走了。
女孩:“……诶?说句话啊?真没礼貌!”
穆康不是故意不理人,而是真的没注意到。他满腹心事地坐上网约车回到家,一路都在想:今晚喝了不少,应该能睡个好觉了吧?
可惜天不遂人愿,他还是在入睡两小时后固定睁眼。
穆康没有失眠,他是被噩梦吓醒的。
噩梦几乎隔天就重来一次,内容千篇一律:穆诗人负责念诗,林狱警负责缄默,两人无计可施地走向阴阳两隔的结局,梦里最后一个画面,是登上山巅、面无表情关上门的林衍。
穆康每看一次就心痛一次,一心痛就吓醒,如斯往复了几十个冬夜,不受控制的大脑丝毫不懂何为吃一堑长一智。
没心没肺活了三十多年的穆大才子一朝开窍,心悸病不治自愈,相思病又无缝衔接。患者吃不好睡不着,被噩梦纠缠得都想约见心理医生了。
整个十月,穆康没接一个新活儿,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一门心思地找人,奈何失踪人口留下的信息寥寥,结果不甚理想。
穆康手中最后一条能用的线索,是普鲁斯特管乐团11月中旬在的演出。他和基金会发了好几次邮件,迁就着那边“三个工作日内回复”的效率,你来我往了半个月才弄明白,演出根本还没确定具体的时间和地点。
和基金会沟通耗时费力,穆康只好转而求助丹尼斯和安德鲁。两位管乐演奏家一开始挺热情,同穆康来回发了几封邮件后,又不知为何没了音讯。
自l市的一夜欢好后,算下来穆康快有两个月没见林衍了。
林指不出手则已,一出手就把穆大才子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。受害人大半夜睡不着,爬起来上跑步机跑了十公里,硬把自己折腾出一身热汗。
房里没开灯,穆康赤裸上身站在落地窗前平复呼吸,嘴里叼着烟盒里的最后一支烟。
烟雾至火星处袅袅升起,穆康捧着手机,在如水月色中点开了来自evanlin的最后一封简短邮件。
一个林衍攒足勇气才留下的只言片语。
一个穆康怎么想也想不通的后悔莫及。
林衍的手写字条被留在了瑞士,这封既无笔触也无温度的邮件,成了穆康唯一的心灵寄托。
他不小心弄丢了心爱的阿衍,忽然(本章未完,请翻页)

![你怎么这么美[快穿]](https://dzdushi.com/image/13/13973/13973s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