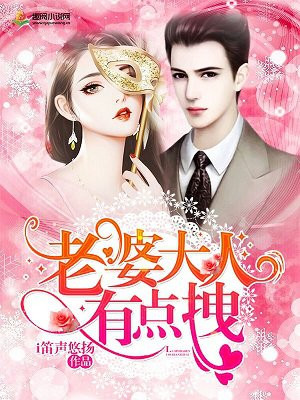赤军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DZ读书dzdushi.com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当日退朝之后,荀崧暗中找到梁芬,问他:“司徒公,朝廷于内外诸事,只是不答不理,长久下去,恐怕威望难振啊,如何是好?”梁芬笑一笑,莫测高深地回复说:“但关中稳固,朝廷威望自高,何所伤也?”
至于关中方面,裴该先接到了熊惕之和梁懃的上奏,二人自然也是相互攻讦,各言彼非。但长安政权与洛阳政权终究不同,情报工作做得相对要好,则对于武都氐乱,裴该几乎同时得着了裴诜的详细汇报,谁是是非,一目了然。
但他先不搭理此事,却急与属吏们商议,问道:“熊悌之既退,复传王处仲也攻巴东不克,返归江陵,则周士达孤军而深悬敌境,情势大为不利,如何是好啊?”陶侃捻着胡须,缓缓说道:“若止孤军深入,尚且无碍,以士达之能,自可勒兵缓退,必不为敌所趁。然而……恐怕王处仲将趁机谋夺襄阳,若襄阳失,士达后路断绝,进退无据,便凶险了……”
裴该一撇嘴:“王处仲、世将兄弟,多半会为此下作无耻之事!”顿了一顿,又说那咱们也没办法啊,终究相隔甚远,咱们既不能再发兵自武都南下,策应周访,也不可能遣将到荆州去,协助陶瞻守备襄阳城……
裴嶷却道:“即便王处仲兄弟夺取襄阳,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进兵与周士达相攻,唯恐彼等断绝粮秣供应,而使周军自乱……可命成方南下供输军粮,使周士达多维持几日,方便筹谋对策。”
“成方”就是裴轸,时为上洛郡守。上洛是司州最西南部的一个郡,南接魏兴,那就可以尝试把府库中的存粮,多多少少给周访送一点儿去应急——“即便杯水车薪,起码能使周士达感德于明公。”
可是谁成想裴诜好不容易搜集起来的三千斛粮草才刚进入魏兴郡内,就传来消息,周访已克汉中。消息传到长安,陶侃不禁慨叹道:“士达诈死破敌,奇谋妙计,自能名垂青史,我所不及也。”
裴该笑着安慰他说:“陶君,何必妄自菲薄,岂不闻‘善战者无赫赫之功’么?周士达用计悬危,乃为王氏兄弟所逼,不得已而死中求活,何足为法。”
随即就跟陶侃、裴嶷商量,说既然周访已得汉中,那武都方面的外患就基本解除了,再加上仇池氐几乎尽灭,则不必要再屯扎一营兵马在郡内——“我意将熊悌之召回长安,别署郡尉,于当地料民为辅兵,镇守诸县,君等以为如何啊?”
裴嶷摇头道:“先不必召还熊悌之,而应行文斥责梁懃,命其来长安谢罪。”
裴该微蹙双眉,问道:“叔父之意是……”
裴嶷笑道:“若梁懃不肯来,正好使熊悌之挥师进剿,除去宕昌之隐患;若其肯来,乃可留于长安,或者置之别郡别县,断绝其族与宕昌羌人的联系。到时别命武都县长,可以徐徐解决宕昌问题。”
不管怎么说,梁懃在宕昌也属于半割据势力,不定什么时候这堆柴草就会燃起火头来的,不可不防。在裴嶷等人看来,即便梁氏占据武都一县,也不为祸,但问题他麾下还有那么多羌人哪,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,晋人世豪尚可容忍,至于氐羌酋大,那得着机会就得给铲除喽。
裴该颔首,随即又问:“武都县内方经屠戮,氐虽灭,羌心亦未必稳固,倘若梁懃应命前来,则命谁继任县长为好呢?彼处晋戎杂处,当用明晰情势之人,方可保安。”
裴嶷建议说:“熊悌之所荐张节理,京兆人士,因胡乱而流亡武都,久在郡内,或者可用。”
裴该想了一会儿,实在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,只得点头道:“如此,可命其先归长安,待我见了,确实可用,再实命之。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裴该在关中统筹诸事,主要是发展生产、训练士卒,同时也亲手指点裴诜搞情报工作,甚至于命裴诜悄无声息地把手伸去东方——
终究裴子羽是自家亲眷,比较可信,王贡则是旧有污点之人,又孤悬在外,裴该对他,实在也并不怎么放心。
等到下令给梁懃,命其亲来长安谢罪的数日之后,裴嶷突然来报,说毌丘奥和杨谦前来求见明公。
这二位一个多月前就逃离巴东了,想要北上关中,但一来路途不熟,二则害怕被王敦、王廙的部下劫住,绑了他们前往洛阳,甚至于直接一刀毙命——王敦多跋扈啊,第五猗是前车之鉴哪——故此反复绕道,历经坎坷,前不久方才抵达长安。
到了长安之后,不敢直接求见裴该——一则身份悬殊,二来又不清楚裴该的态度——毌丘奥乃直谒裴嶷府门。裴文冀为行台长史,倘将雍、秦目为一国,则他就是首相,自然门庭若市,毌丘奥本是弃守私逃的罪臣,不敢大肆声张,只好老实排队,就这样连排三天,这才终于见到了裴嶷。
而且他都不敢打出巴东监军的旗号来,所投名刺上只写“通家故人”。
无论长安、洛阳,还是建康,此前确实基本上就把巴东郡给遗忘了,虽未陷敌,也与别国无殊,直到周访伐汉、李寿取巴,裴诜搜集了前线的军情,三天一次向裴该禀报,裴该再与裴嶷、陶侃等商议,众人才终于得知杨和毌丘二人之名。所以裴嶷见到名刺就笑啊,心说毌丘奥兵败后不投洛阳,却来长安,此事大是有趣……
即命召见,毌丘奥一进来就伏地大哭,谴责周访不肯相救,然后又曲曲折折,表述自家与裴氏的世代交好——即便没有这一层,那也是闻喜老乡啊,岂可不互相关照一二?
裴嶷命其与杨谦暂时等候,自己前来向裴该禀报,裴该说这般弃职失土的庸人,咱们又何必理会呢?绑缚起来,押往洛阳可也。
裴嶷摇头道:“不可,彼等远道而来,专投文约,则若文约不纳,恐失四方人心哪。”随即帮忙解释,说人各有所长,也有所短,杨谦、毌丘奥本不擅长军事,遭逢强敌后,周访又不肯救,无奈而逃,也属情有可原……
“相距不远,而周士达方致力于汉中,竟不发一兵一卒往救,遂使国家土地,没于贼手,此曲在士达,毌丘等实在可悯。”
裴该闻言,不禁撇了撇嘴,叹息道:“周士达,官僚也。”
在裴嶷听来,这大概是一句好话,但其实裴该所言的“官僚”,是取后世“官僚主义”之意——官僚主义中很重要的一条,那就是罔顾大局,只扫自家门前雪。裴该自忖,倘若我是周访,只要无伤于攻伐汉中的大业,邻郡之难,那是肯定要伸手去救一把的。若非如此,你周访是胜是败,关我何事啊?我要在关中为你担忧,还特命裴轸供输军粮于汝?
但是官僚习气,普遍存在,周士达亦不能免俗,况且说不定,他还希望巴东失守,好让王敦前进时去碰一个大钉子呢。其实此番攻伐汉中,本来就是王敦和周访内斗的结果,裴该又岂能不知啊?
故此他才口出“官僚”二字——周访虽为名将,终究不脱陋习,人无完人,岂不可叹?
于是便问裴嶷,该怎么处置杨谦和毌丘奥二人为好?
裴嶷拱手道:“查实杨谦,实为弘农杨氏孑遗……”
裴该编《姓氏志》,把弘农杨氏列在第九,但事实上这一东汉以来的经学高门,早就处于半绝灭的状态了。
杨氏家门烜赫,始于“关西孔子杨伯起”,也即东汉太尉杨震。杨震的后裔主要分为两支:一支主事于汉末,传杨彪、杨修;逮入晋后,杨修之孙杨准官至冀州刺史,且与裴頠相交莫逆;杨准有子杨峤、杨髦、杨俊,伯仲皆至两千石,杨俊为太傅掾,却皆没于“永嘉之乱”。
第二支传至杨骏杨文长,初不过以县令入仕而已,但其女嫁与晋武帝司马炎为后,就此以姻戚之贵而平步青云。然而杨骏既非弘农杨氏的主支,本人才能也极其有限——不如其弟杨珧、杨济远矣——故此而为士林所轻视,这更导致他任人唯亲、施政苛碎,最终被贾南风召楚王司马玮入京所杀,三族夷灭。
所以到了裴该留台关中的时候,弘农杨家已经找不出几个人来了,之所以在《姓氏志》中仍列高位,一则是初纂者董景道仰慕杨震之故,二是裴该为了平衡各方势力,而特意设下的圈套。毋庸置疑,倘若杨家在数年内再不能出二千石以上高官的话,名次肯定要大幅度下跌,空出位子来以待关西家族的晋升。
但是裴嶷说了,杨谦就是弘农杨氏,虽然不是杨彪或杨众(杨骏祖父)的苗裔,却也相差不远——他就是二千石啊,只是从前没人意识到还有此人罢了……
“至于毌丘,出于妫姓,为古毌国之后,渊远亦长,入魏后一度烜赫……”
毌丘兴仕魏为武威太守、将作大匠,因讨叛胡有功,封高阳乡侯,其子毌丘俭则一直做到镇东将军、扬州都督。
大致介绍了一下杨谦和毌丘奥二人的家系后,裴嶷就提出来:“文约,岂不闻‘兴灭国,继绝世,举逸民,天下之民归心焉。’”这句话出自《论语》,是指恢复已灭之国、已绝之贵族家系,那是可以刷声望的——
“倘能使杨谦复兴弘农杨氏,则必感德于文约;能将毌丘复置于闻喜,必为我家臂助。”
事实上,裴嶷对于裴该大批提拔寒门士人,心里是并不怎么以为然的,在他看来,这只是乱世中人才不足的情况下,无可奈何的临时举措,终不能为万世成法。他希望裴该能够扶持在最近几十年甚至更久远一些,直至魏晋易代之时,那些日趋衰微的大家族,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基础,扩大自己的联盟势力。
所以今天逮着一个姓杨的,一个姓毌丘的,就急忙跑来劝告裴该,不可断然拒之于千里之外,还是趁机笼络为好啊。
裴该沉吟少顷,回复说:“弘农杨氏还则罢了,毌丘乃叛臣之后,何必用之?”
他的想法自然与裴嶷不同,因为即便把汉末以来的经学大族全都复兴起来,总体数量也不过尔尔,想靠着如此低比例且极其固化的阶层来巩固统治,必然导致政权的不稳和内卷化。他之所以一定程度上扶持寒门庶族,就是为了打破世族地主的垄断地位。
但这话不便明确宣之于口,更不方便跟裴嶷提起——人屁股可是稳稳地坐在世族一边的——故此裴嶷想要复兴弘农杨氏,还端出“存亡续绝”的儒家大义来,裴该是不便阻止的。况且他再一琢磨,这和李容所言,对于河东世家要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,或许也可起到异曲同工的效果。
左右不过一个杨谦而已,便应允了裴文冀,又打什么不紧?只是那毌丘奥……毌丘氏原本就算不上什么巨族,尤其毌丘俭还被满门夷灭,如今就剩下毌丘奥这么小猫三两只,有必要加以扶持么?
裴嶷笑道:“毌丘俭所叛,魏也,与我晋何干啊?”
其实毌丘俭是谎称得到郭太后的手诏,打着扶魏的旗号,叛攻的司马师,但当时司马师为曹魏执政,他当然不能承认了,对外必须宣称毌丘俭叛魏。那么魏为胜国,都亡了很久啦,魏之叛臣,咱们有啥不能用的?
再者说了,毌丘奥本身也是晋臣嘛,也没见司马家再提起往事来,说应该把这条当初的漏网之鱼也一并铲除喽……
关键是——“我裴氏根基,终在河东,则毌丘闻喜人也,既然来投,岂可严拒之?”
裴该心说我让李容去削弱河东大族,幸亏这事儿没跟叔父你提,否则你非跟我急不可……当下微微一笑:“叔父所言是也,然而这般庸懦颟顸之辈,恐不宜入我行台。”终究二人镇守巴东那么些年,不能够安百姓、固防守,以御贼人来侵,顷刻间便即失地弃守,不必亲与交谈,也知道不会是什么有本事的,则我若用了他们,被他们带坏了我关中行台的风气可怎么好啊?
裴嶷反复劝说,裴该只是不允,最终裴嶷无奈之下,只得退而求其次:“彼等来此,是恐朝廷治其失土之罪,文约还当为其缓颊,以笼络人心——机会不可失也。”
裴该点头说,这倒没有太大问题,我命郭璞写一封上奏,帮那俩货求求情,免了他们的死罪,也就成了。裴嶷摇头道:“不可,彼等不往洛阳,而先来投关中,复又归之洛阳,恐朝廷质疑文约越俎……”终究巴东不归行台管,你有什么理由为巴东守将求情啊?
最终商定,命郭璞作书,裴该署名,交给杨谦、毌丘奥,让他们持此书信,到洛阳去拜谒荀崧,请荀景猷帮忙缓颊。如此一来,裴该既无越俎代疱之嫌,那二人也仍然会感念裴该的恩德,勉强可算是两全。
.。m.
www.。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