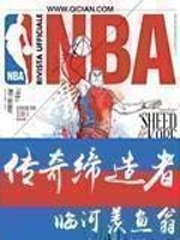赤军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DZ读书dzdushi.com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荀灌娘问卞壸在想什么,卞望之就说啦:“郗道徽之为人,素来谦抑、谨慎,虽好酒,即便沉醉,也从无妄语。今藉酒逃席,却云‘恨不能跻身裴、祖二公之幕’……得非其心已动乎?”
荀灌娘说既然如此,那他为什么跑了呢?
卞壸有些不确定地回答道:“想是席间人多,不便明言……”要都是我们大老爷们儿也就算了,这儿还好几个女人啊,郗鉴有什么想法,肯定不肯当着女人的面说——“且夫人今日所言,未必咄咄逼人了一些。”
荀灌娘心说好嘛,敢情还是我的错……若真是男人,是留或是不留,就该直截了当地表态,怎么还装醉、逃席,比女人还要磨叽!这世上果然只有我老公才最高,其他皆不足论!
正在郁闷呢,就听卞壸说:“时辰未晚,夜尚未深,壸当亲往探其真意,还请夫人稍待。”
于是卞壸辞别了荀灌娘,先把老婆孩子送回住处,然后就独自一人驾车去探望郗鉴,那意思:你不是很能喝吗,怎么今天醉得这么快?是不是身体有何不虞,让我瞧瞧,要不要请个大夫过来……
郗鉴果然开门迎入卞壸,双方才一坐定,他就问了:“卞君有言,乃可明与我说,为何假口于裴夫人?”
卞壸笑道:“裴使君甚重卞公,每欲招揽,裴夫人亦有耳闻。本欲在今日宴间,探问卞公所思所想,因与裴夫人说起,彼乃相为助言耳。高门贵种,又是妇人,所言或有不当,得罪卞公处,壸替她在此谢罪了。”随即便拱着手,深深鞠下躬去。
郗鉴赶紧提双手搀起卞壸来:“君何必如此,且……裴夫人之言,亦不为无理,只是……”压低声音说道——“我实不忍背刘将军,此忠诚之心,妇人难明,卞君当能知我。”
卞壸心说闹了半天,你还是不肯留啊,便即劝说道:“为郗公计,厌次实属险地,不可久居,何如留在淮阴,于私可得保安,于公亦可做大事业——裴使君之才、之志,非同凡俗,郗公或未知也,且待……”
郗鉴摇摇头,打断他的话:“我意已决,卞君不必再劝,且……”略笑一笑——“君之词锋,不如裴夫人远矣。”然后他抓着卞壸的手,又说:“若厌次有事,还望徐方加以援手;我若侥幸得生,自当南依裴公,与卞君共事。今仍将妻儿托付裴公、卞君,若能使郗门不绝,我即死,亦当于地下感念二位恩德。郗迈为家兄遗子,家姊所留亦止周翼,二子虽幼,尚肯勤学,今一并托付,还请勿辞。”
郗鉴的意思很明确,我是奉了刘演之命南下的,结果走半道儿就留下了,不回去了,如此辜恩失信,还有什么脸面在世为人呢?我是一定要回厌次去的!但考虑到那地方确实危险,我不能让老婆孩子,以及侄子、外甥跟着我一起冒险啊,他们就都留在徐州吧,还请你和裴使君多加照顾。
话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了,卞壸也不好再劝——好在最初的目的达到了,起码没让你把老婆孩子全都领走。无论徐州还是豫州,目前的战略目标都是中原和关西,河北的石勒只好先放着,有石勒在,厌次危若累卵,沦陷只是时间问题罢了,到时候郗鉴若是罹难了,命该如此,无法可想;可要万一你还活着,老婆孩子、侄子外甥都在徐州,不怕你不过来啊。
当即拍拍胸脯,一力担承,正打算就此告辞,郗鉴却仍然扯着他的手,不肯松开。卞壸把疑惑的目光投向郗鉴,就见郗道徽面沉似水,开口问道:“如卞君方才在席间所言,裴公、祖公,皆已兵入河南,且破刘乂;刘粲亲统大军南渡,或许这一两日,便要决战——可有几分胜算哪?”
卞壸笑笑,回答道:“我不通军事,郗公未免问道于盲了。然而,前此阴沟之战,我徐州两千兵遭遇刘乂所部胡贼不下五万,激战整日,而不言败,复陶士行以舟船绕之敌后,贼众大溃。以此看来,裴使君常云我徐州兵精锐,是非虚言也,况有祖士稚、陶士行在,则与胡决战,获胜可期——或许胜报已在途中,特未抵达淮阴耳。”
郗鉴沉吟道:“我自河北南下,入徐后先东莞,次琅琊、东海,见残破之状,与中原无殊;直至下邳,始略有振作之象。然入临淮、广陵,见田地得垦殖者,十不二三——即为大雪所覆,是否熟地,鉴也能分辨一二。似如此,何来的兵精,何来的粮足?”
卞壸拍拍郗鉴的手,回答道:“徐方户口,本与青州无可并论,遑论司、冀?然之所以能得兵精粮足者,特因裴使君召聚流民,于邯沟以西辟沃土屯垦之故——郗公若不急于南下,明日我可引公前往观看——其后虽有部分编户分地,亦多在郡东。即不论全徐,便临淮、广陵二郡,若户口繁盛,一如昔日之司、冀,裴使君必可兴大军十万,岂止区区两万而已。”
“原来如此,”郗鉴点点头,“未知是军屯啊,还是民屯啊?”
“军民两便……”于是卞壸就把徐州屯田的情况,大致向郗鉴介绍了一番。郗鉴笑道:“是如曩昔魏武在兖州也……但愿苍天护佑,此番河南之战,能得大胜,长安之围或解,而胡贼退守河东、河内,三两年内,不再为中原之患也。”随即眉头微微一皱:“唯羯贼既占临漳,其势日炽,亦不可小觑啊——或将来我晋之大敌,不是胡虏,反为羯贼!”
——他也是曾经被石勒俘虏过的,跟石勒、张宾等人全都打过交道,深知那几位都是极其危险的角色。
卞壸点头道:“裴使君亦尝做此语。本待挥师北上,先平羯贼,奈何长安告警,天子危殆,身为臣子,又岂可不前往援救呢?”
郗鉴凑近一些,压低声音问卞壸:“鉴有一语,不知是否当言……”卞壸说这大半夜的,就咱们两人在堂上,那还有什么不能说的?
郗鉴犹豫了一下,最终还是说道:“前裴公常有书信与我,云建康但谋割据,无北向中原,恢复故都之意。我初始亦不信,然数年来,刘将军亦曾遣使至江东,归言所见所闻,可知裴公之语不虚。则今岁骤然下令徐、豫北伐,应是驱虎吞狼之计。倘若二公战败,江东必谋二州;即二公战胜,恐亦将以他事勒令退兵,若不从时,乃负叛名,二州亦将落入建康之手——不可不虑啊。”
卞壸同样压低声音说道:“此事早在使君料算之中。”
“哦,未知如何计议,可肯相告否?”
卞壸说:“初论及此事者,裴文冀也,然云无可深忧。当北伐之际,若江东即遣军袭取徐、豫,师出无名,必罹骂声。北人初渡,不过数载,南人无不侧目,本便龃龉丛生,若建康有害国之事,诚恐祸起萧墙,料王茂弘必不行此下策。而若前方得胜,急令退兵,乃可以‘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’搪塞之……”
郗鉴有些不以为然:“此又如何搪塞?”
卞壸笑笑:“即无可搪塞,建康欲兴师北伐,然谁人可遣?建康守卒不过一两万,且王茂弘、庾元规书生耳,无能为也;王处仲若发兵,首当其冲为豫州,不及徐方;周士达南人也,安肯为彼等谋取江北土地?前此杜弢、胡亢祸乱荆、湘,建康群臣相互推诿,迟至半岁,始得发兵,则欲谋徐、豫,又当迁延多少时日?其军尚未动,而二公必已归矣。”
郗鉴这才略略舒了一口气:“如此便好——其实二公不必急归,不若速速西进,以求天子诏,若得天子嘉勉,建康无能为也。”
卞壸点点头:“郗公所言是也,我当密书以告裴使君。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其实郗鉴和卞壸在商议此事的时候,建康政权就已经发出了退兵的指令,一力促成其事的不是王导,而是庾亮。王导问庾亮:“今胜负未分,而急命二州之兵南归,若其不肯,如何处?”庾元规回答说:“若彼已败,不必申令,自然归州;若彼得胜,而命其归,是必不肯从也!今闻大军粮秣不继,而胡贼已将主力汇聚河南,我料祖、裴正进退两难之际,则退兵令下,安有不肯之理?”
庾亮也算当时有数的政……政客,但他最大的弱点有二:一是行事操切,往往不肯仔细考虑后果;二是自视过高,觉得自己办不成的事情,别人也肯定办不成。那么北伐大军只有四万——裴该对江东虚报了自家的出兵数量——听说刘粲领了六七万众南下,换自己是主帅,这仗敢打吗?肯定不敢啊!
或许祖逖胆子比自己要大点儿吧,敢于冒险,但别忘了边上还有一个裴该呢——裴文约不过一介书生耳,北渡徐州是专门为祖逖去种地搞后勤的,此前最多也就领着五千人去灭过第五猗,复在江上耀武扬威了一回而已,但第五猗那路货色,能跟凶悍的胡兵相提并论吗?
他琢磨着,祖、裴二人一定在是战是守的问题上争论不休,进退两难——进,基本上打不赢;退,这面子往哪儿搁啊?
王导皱着眉头,追问道:“设若二人坚不肯退,又如何?”
庾亮说又如何——“即可申以违命之罪,发兵讨伐,进取豫、徐,以广我建康声势。”
“江南之兵,自保尚且为难,何人可以北渡以讨伐之?”
“乃可命尊兄处仲北取豫州;周士达挟镇定广州之势,以向徐方,”庾亮笑一笑,“关键在于,祖、裴二人岂不虑此,则焉敢违命?”
二人商议了好半天,最终王导拗不过庾亮——王茂弘的弱点就是不够强势,尤其压不住小兄弟庾元规——只得允其所请。当然啦,他们也不是没有考虑到,万一祖逖、裴该去请天子诏又如何,但天子见为索綝挟持,诏书是能那么容易拿到手的吗?
最主要的问题,他们对于北伐军真能够打赢,镇定河南,根本是毫无信心,所以本能地就忽略了此事……
但其实建康的指令还没送抵河南,裴该和祖逖合兵一处,就已经拿下了偃师,进而祭扫首阳山上的历代皇陵,大军浩浩荡荡直向洛阳而去。等到指令传到,二人正在洛阳城内巡视、吊怀,祖逖闻报大惊,就待回营去问个究竟,却被裴该揪住了马头,裴该说你不能去啊——咱们得先商量定了,再可归营。
因为这事儿是瞒不住的,到时候兵将得闻——主要是豫州那些坞堡主——人心思归,你还怎么驱策得动?于今之计,是先拖延时间,你留镇河南,我急率兵西进去救长安,请下天子诏来,便可破解建康的图谋。
议定之后,方才归营,请了退兵令来看。建康方面的借口是:闻石勒已克临漳,即将会合曹嶷,南下攻打徐方,进而渡江侵扰,为保建康不失,北伐暂停,卿等可率部急归……
裴该见了,不禁“哈哈”大笑,说:“此风言妄传耳,不想建康诸公如此庸怯,竟为流言所蔽……”在诸将面前,不方便把那些懊糟的勾心斗角事合盘托出,所以他就只好这么说啦——“前此我已遣人说降了曹嶷,想是归附之使,尚未抵达建康耳。而即石、曹联兵,欲侵徐方,距之江南尚有千里之遥,又有何忧?”
当下便即写下一封书信,与祖逖共同署名,请使者带回建康去——这是为了拖延时间。随即两军各自开会,豫州军那边,祖逖说如今形势大好,怎能够轻易退兵呢?琅琊大王受了流言所扰,咱们给他解释清楚就行啦——先不必退,我等暂留河南,以待后命。
至于徐州这边儿,裴该话就说得很清楚了:“此建康诸公忌妒我等,不欲使我等立功也!”这是一招激将法,果然诸将闻言,全都怒了,纷纷鼓噪——只有陶侃一人低垂着头,不言不动。裴该说了:“为今之计,只有先挽留东海大王,使勿先退,我等则急向长安,救援天子,请天子下诏,则可无虑建康矣。”左右望望:“谁愿请令?”8)
www.。m.